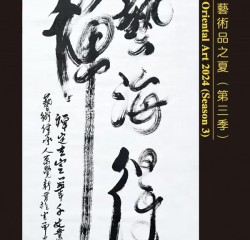我们对梵高了解得太多,又太少

文森特·梵高,1853年3月30日-1890年7月29日
1853年的今天,画家文森特•梵高诞生。他一生创作超2000副作品,将所有孤独和苦难转化为热情洋溢的色彩,用绘画展示对生活的爱与激情。
梵高诞辰169周年之际,文学陕军邀您共读《梵高手稿》。致万物花草,致街巷酒馆,致宇宙星空。
荐读:
灵魂如果有高度,那应当是生来怀有对世界的爱与责任的文森特•梵高。
【1880年7月】 No.133
换羽期对于鸟儿来说,就像我们人类面对逆境或者不幸一样,是痛苦的时期。你可以选择停留在痛苦中,也可以由此脱胎换骨,重新做人。但是,这并不是一件值得张扬的事,也不是一件可以调侃的事,正因如此,你才需要藏起来。好,那就这样吧。
如果你能体谅一个人献身于绘画研究,就要理解热爱读书和热爱伦勃朗一样神圣,我甚至认为这两种热爱相辅相成。
所以你追求的是什么?人的外表是否能反映他的内涵?人的灵魂里都有一团火,却没有人去那儿取暖,路过的人只能看到烟囱上的淡淡青烟,然后继续赶他们的路。
那我们要做什么?给心中的火添柴,“你里头应当有盐”,不管多焦躁,也要耐心地等待,等到有人想要来访,在火边坐下来——待在那里,我怎会知道?任何信仰上帝的人都能等到这一刻到来,或早或晚。

阿尔盛开的果树园
眼下我似乎事事不顺,而且这样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,或许还会持续下去,但也有可能否极泰来。我并不指望这样,可如果真有转机,我会认为这是莫大的收获,我会很高兴,会说:“果然不出所料,这一天终于来了!”
我就这样随意写下涌到笔尖的东西。
如果你不把我看成那种游手好闲之人,我会非常高兴。
即使游手好闲者也有不同的类型,有种人因为懒惰、卑劣、缺乏个性而碌碌无为。如果你愿意,可以把我看作这类人。
也有另一种人,尽管他们的内心被强大的渴望所驱使,但现实不可改变,他们无能为力,就像被囚禁了一样,所处的环境缺乏创造所需的土壤,使他们无所作为。这样的人不是总能确定自己要做什么,但是他本能地感到:尽管如此,我必然有擅长的事情,我必有存在的意义!我知道我会成为一个不同的人!只是我如何能成为有用之人?应该怎么做?是金子就一定会发光,但我身上能闪光的特质又是什么?
这是意义完全不同的游手好闲,如果你愿意,也可以把我看成这类人。
春天的时候,笼子里的鸟儿跃跃欲试,它知道自己生来擅长某事,也强烈地想要去做,但又无法做到。是什么?它却无从知晓,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,“其他的鸟儿都在筑巢,孵化、哺育雏鸟”。于是它用头去撞笼子,笼子完好无损,它却因悲伤而发狂。
“真是个懒骨头!”另一只经过的鸟儿说,“它活得真舒服。”被囚禁的鸟儿没有死掉,它活下来了,心里想什么从不外露。它恢复了健康,阳光和暖的时候,它多少也会开心一会儿。然后迁徙季节到了,它心中又一阵悲凉,“但是,”照看它的孩子们说,“所有的必需品,笼子里都有呀。”但对它而言,这个“都有”只能意味着望着外面酝酿暴风雨的低沉天空,心里升起对命运的反抗 :“我在笼子里,在笼子里,所以我什么都不缺,蠢货!我有一切我需要的东西!哦,看在上帝的分儿上,给我自由吧,像其他的鸟儿一样。”
那个游手好闲的人,就像这只无奈的鸟儿一样。
人们也常面临着无能为力的情况,如同被困在这样令人恐惧的笼子里。
我当然知道会有解脱之时,最终的解脱。是什么把人变成囚徒?是因揭发或造谣而败坏的声誉,是尴尬之情,是不安之境,是不幸之事。人并不是总能知道什么囚禁了他,什么样的墙把他隔绝,或者什么把他活埋,但是总能感觉到那些像闩条、像笼子、像墙一样的东西无处不在。

皇帝蛾
所有这些都是想象抑或幻觉吗?我觉得不是。于是我扪心自问:我的上帝,这种境况是长久的吗?是永远的吗?还是永恒不变的?
你知道什么能让这无形的囚牢消失吗?是每一种深刻而真实的爱。是朋友之谊,是手足之义,是情人之爱,正是爱至高无上的力量才能打破这无形的囚牢。没有爱的人,毫无生活可言。
情义被唤起之处,生命得以重生。
有时候,这个囚牢也会以别的名字出现,比如偏见,或误解,或对这或那的致命无知,或不信任,或假意的羞耻。
【1883年4月】 No.278
谢谢你美好的生日祝福。生日那天我相当高兴,因为我找到了一个极佳的挖掘者当模特。
请你放心,工作越来越让我感到愉悦,或者可以这么说,更多是一种工作带来的内心的慰藉。这让我想起你,正是有了你的帮助,我才得以工作。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,没有任何的绳索桎梏。有时候,困难也是一种激励。现在是再加把劲的时候了。我的理想是画更多的模特。在寒冷的天气里,在失业中,在需要帮助时,画室可以成为穷苦人的某种庇护天堂。他们知道画室有温暖的壁炉,有吃有喝,而且还能挣一点小钱。现在规模尚小,但是我希望人数会增加。
【约1883年8月4—8日】 No.309
我对通过多加练习来提高对颜色的掌握这件事,抱有很高的希望。对我来说,最后这幅画的颜色更好更坚实。举个例子,我最近画了些雨中景物,行人走在潮湿泥泞的路上,我觉得这种氛围的表达恰如其分。
大部分画都是风景的印象。并不是说它们都像我在信里展示的这些一样好,因为我常常遇到一些技术难题,但这些画作中依然有些可取之处——比如,小镇的轮廓映衬在夕阳的余晖中,拖船的纤道和风车。

在圣马迪拉莫海边的渔船
对色彩的确定感,最近也开始在我心中活跃起来,当我画画的时候,开始有了不同以往的强烈感受。我总想画得不那么干巴巴,但是每次效果都差不多一样。不过好在只有那几天而已。现在身体原因让我不能像以往那样画,但这对我的帮助胜过影响。我画画的状态更放松了,不再专注于衔接和分析如何将事物组合在一起,而是更多地透过睫毛去看,更直接地观察事物,把它们看成拼合在一起的不同色彩块。我非常好奇这种观察方式会带来什么成果。我有时候很想知道为什么自己没有成为调色师,因为你会觉得以我的性情,应该很擅长才对,但迄今为止,我的进步还是少之又少。我时常担心在色彩方面没有明显的进步,但现在我又有了些希望。我们拭目以待吧。我想说的是,事实上,我相信这些习作中,比如说透过睫毛观察自然,可以得到些神奇的效果,形状就会简化成不同的色块。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,但现在,我在很多不同的习作中,看到了色彩和色调的变化。
又及:
这只是一个怪念头,也没有什么特殊原因,我想加几句刚想到的事情。我不仅很晚才开始绘画,更为严峻的是,或许我也难指望能再活很多年。如果用冷静的分析去预测或计划这段时间,那么,自然地,我也无从知晓。
但是如果与很多我们了解其生活的人,或者与那些和我们相似的人对比,就可以做一些有根据的推断。
在接下来还有余力工作的时间里,我可以接受的事实是,我的身体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,如果一切都没事的话,大概是六到十年,这个假设并不草率吧。我愿意接受这个长度,更重要的是,因为眼下没什么可担心的。这个时间段,是我最可靠的指望。其他的方面充满了变数,我不敢随意揣测,比如,过了之后还有没有时间,很大程度取决于第一个十年的结果。
如果这些年总是劳累过度,一个人很难活过四十岁。如果一个人可以让自己从人们常遭受的打击中恢复过来,并且克服相对复杂的身体疾病,那么你从四十岁奔向五十岁时,就能过上崭新且相对正常的生活了。
如我所说,未来五到十年的计划我也考虑过,但是目前并不在我的日程上。我的计划不是要救自己,也不是要避免太过情绪化或者太多困难——对于活长活短,我并不关心。并且,我也没有医生的本事,去引导自己身体力行。
因此,我不在意这些事情,继续我行我素,但是有一件事是明确的:我必须在有限的几年中完成一定数量的创作。我并不急于求成,因为这样做显然不可行,但是我必须要平静而沉着地继续创作,尽最大的可能有规律地、全心全意地去画画。
我在世上唯一的顾虑,就只有对这世界未尽的义务和责任,活在世间三十载,我还亏欠它一些可以流传后世的素描和绘画作为纪念品,不是为了某些特定活动应景作乐,而是为了在画中表达纯真的人性。这就是我的目标,而专注于这个想法,就可以让判断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变得更简单,也能使我免入混沌的歧途,因为我的一切作为,都是出于这个愿望。
荐读:
他懂自己,懂所有的可爱与快乐,懂所有的深刻与通透。愿我们都能拼劲一生奔赴在自己的热爱里,不疑己身,不负所遇。
【约1882年4月15—27日】 No.190

挖掘者素描
附上一张挖掘者的小素描,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发这幅画给你。
特斯蒂格对我说:“你以前事事不顺,常常失意,现在也一样。”让他住嘴吧,绝对不是这样的,情况今非昔比了,他这么说是大错特错。
我不适合从商或做学问,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不适合当画家。恰恰相反,如果天生适合做牧师,或者帮别人卖画,那我可能就不擅长画画,也不会如此决绝地放弃那些工作。
正因为我有一双天生要画画的手,我绝不能放下画笔。我问你,自从我选择开始画画,我可曾有过半点疑惑、犹豫和彷徨?我想你是懂的,我犹如战场上的士兵一样斗志昂扬,当然,仗打得越来越激烈了。
现在说说这张素描吧,画于吉斯特,那天下着毛毛雨,周围的街道上喧闹纷杂。我发给你是想让你看看,我能捕捉到一些转瞬即逝的瞬间,我的素描本就是最好的证明。
比如,你可以想象一下,特斯蒂格站在吉斯特的沟渠边上,亲自看工人们装配水管或天然气管道,我真想看看他的表情,看他能画出什么样的素描。对于艺术家来说,只有混迹于工坊、大街小巷、房里屋外,甚至酒吧,才是好玩的事。一个艺术家,宁可在这些破破烂烂的地方,找寻可画的素材,也不要故作优雅地去和美女喝下午茶。除非他要画美女,那画家也能去享受一下茶会了。
总之,我想说的是,寻找绘画素材,来往于劳动者之间,反复焦虑着怎么处理模特,身临其境地去捕捉事物最自然的状态,是个苦差事,有时候更是脏活累活。而且,说真的,销售员的衣着和举止,适合那些需要和美女绅士攀谈,并向他们推销奢侈品的人,而对于一个要画吉斯特深井中的挖掘工人的画家来说,并不合适。
倘若我能胜任特斯蒂格先生的工作,那我肯定不会是个好画家。对于我的职业来说,最好的状态就是保持自我,而不勉强去接受根本不适合自己的风格。
要是衣着得体地站在一个体面的商店里,我会浑身不舒服,以前这样,现在更是。我极有可能变得很无聊、令人生厌,但在吉斯特的荒地或者沙丘这种地方的时候,我就变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人。在那儿,我丑陋的脸、被岁月磨砺的外套和那里的环境相得益彰,在那里,我才是我自己,才可以愉快地工作。

从靠码头的平底船卸货之工人
说到“如何去做”,我希望我能找到一条自己的道路。如果我衣着光鲜地去找工人模特,他肯定要吓坏了,要么会怀疑我的企图,要么会跟我要个大价钱。
现在我和以前一样混日子,你可不要认为我和那些抱怨“海牙根本没有模特可画”的人一样。如果有人对我的文明教养、衣着相貌、言谈举止指指点点,我该怎么对待——这种话真烦人?在另一种意义上说,我是不是成了迟钝、没教养的粗鲁人?
应该这么说,好的教养规范应该是关照到每一个人,基于每个有正当追求的人的需求,对每个人都有意义、有益处,而终极需求是为了使人们和谐共处而不被孤立。这就是我尽力在做的,我画画,不是要去惹恼他人,而是让他们觉得开心,让他们发现那些亟须关注但又被人忽略的事。
我无法接受,提奥,我怎么就成了一个粗俗、没有教养的怪物? 好像我就活该被社会排斥,更有甚者,按照特斯蒂格的说法,“在海牙根本活不下去”。难道我深入绘画对象的生活,就是降低人格吗?难道我走近工人们,走进穷人的房子或者请他们来我的画室,就是自轻自贱吗?
我觉得这是我专业的一部分,只有对艺术毫无概念的人才会对我提出质疑。
试问,《图画》周刊和《笨拙》周刊的插画师们在哪里找的模特?难道他们不要亲自到伦敦最穷困的街区找吗?你说是不是?
难道这些插画师生来就了解人?还是他们生活在所画的模特们中间,多年之后才真正地了解他们,感悟到人们未曾经意的,记录下人们已经忘却的?
【1882年8月19日】No.226
上周,我这儿一直在刮大风,伴随着风暴和大雨。我还特地跑到斯海弗宁恩的海滩上去写生,带回来两幅海景小作。有一幅沾上了很多沙子,另一张在画的时候,风浪正大,海水不断涌上沙滩,有两次我不得不把画面完全刮掉,因为画上盖了一层厚厚的沙子。风实在太大了,把我吹得东倒西歪,黄沙漫天,几乎什么都看不清。

斯海弗宁恩海景
但我还是想试着恢复它。我跑进海滩后边的一个小酒馆避风,把画刮干净,马上再把它画出来,然后再跑回风暴中继续观察。所以,我的画上还残留着一些风沙的纪念品。
近来,斯海弗宁恩海滩真是美极了。风暴来临前的大海比狂风中更加气势恢宏。在狂风中,看不到那么多海浪,也看不到那么多像犁过的耕地一样的层层波涛。波浪涌得太快,后浪推前浪,强烈的波浪撞击产生了大量飞沙一样的浮沫,在海面前方形成了一层薄雾,宛如为大海蒙上了神秘的面纱。而这还只是一场狂暴的小暴风雨。尽管如此,你越长久地注视大海,就越为之赞叹,海上几乎没什么声响。大海呈现出脏肥皂泡一样的颜色。海面点缀着一艘小渔船,或许是船队中最后一艘未归航的船,船上还有几个暗色的人影。
绘画带给人的感受是无限的,我无法确切地描述。但我想说,用绘画来表达情绪的过程,简直太美妙了。色彩的和谐与对比,一些不为人知的方面是,它们相辅相成,且密不可分。
我希望明天还能去户外写生。
【1888年8月6日】 No.518
今晚煤气灯点亮后,我可能就要开始画我住的这个咖啡馆内部了。
在这里被称作“夜间咖啡馆”(这种咖啡馆在这个地区很普遍),通宵营业。那些“夜行客”没有钱投宿或者醉得太厉害而被拒绝的时候,可以在这儿挨一晚。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,所有这些——家庭、故乡——或许在幻想中比在现实中更有吸引力,我们在现实中没有家庭和故乡,也过得不错。我总觉得自己像个旅行者,要去向某地,朝着某个终点。若我能感知到这个地方,这个现实中不存在的终点,那么对我来说似乎更加合理,也更真实。

拉马丁广场的夜间咖啡馆
荐读:
这是一封未寄出的草稿,是梵高离世时在他身上发现的。
然而,一切都在这封信的末尾戛然而止。
【约1890年7月10日,弟弟、弟妹】 No.649
我一回到这儿就开始工作了——尽管我几乎拿不稳画笔,但是我对自己的追求了然于心,到现在已经画了三幅大的油画。
画的都是暴风雨天空下漫无边际的大片麦田,我在传达悲伤和刻骨铭心的孤独感时,非常得心应手。希望你们很快就能看到——因为我希望可以尽快把它们带到巴黎去,因为我觉得这些油画可以将那些我无法用文字表达的都告诉你们,让你们知道我在这田园中所发现的盎然生机。第三幅是杜比尼的花园,一幅我刚到这里就开始构思的画。

暴风雨下的麦田

麦田群鸦
【1890年7月,弟弟、弟妹】 No.650
我已经完全被这一望无际的平坦麦田和山丘所征服。如大海一样的辽阔,娇嫩温柔的黄色、浅绿色和紫色,耕过的田野已经除完了草,绿色的土豆花点缀在田野中。所有这些都铺展在细腻精巧的蓝、白、粉、紫色的天空下。画这幅画的时候,我全身心都沉浸在一种平静的心境中。
【1890年7月23日】 No.651
也许你会想看看这幅杜比尼花园的素描稿——它是我最深思熟虑的一幅油画。我也附上了一幅收割后的麦茬田的素描。还有两幅30号油画的素描,画的是雨后绵延广阔的麦田。杜比尼的花园,前景是绿色和粉色相间的草地。左侧是绿色和淡紫色的灌木丛以及一些长着泛白叶子的低矮灌木。画面的中央有一个玫瑰圃,右侧有一道围墙和小门,墙的上方是蓝紫色叶子的榛树。丁香的树篱,一排修剪成圆形的黄色椴树,粉色的别墅掩映在背景中,屋顶上是泛蓝的瓦片。画中还有一把长凳、三把椅子和一个穿黑色衣服、戴黄帽子的人。在前景中还有一只黑猫,天空则是泛白的绿色。

杜比尼的花园与黑猫
【1890年7月24日】No.652
坦白地说,画家只能用画来说话。不过,亲爱的弟弟,就像我反复和你说过的那样,我再次严肃地向你强调,用一个人的头脑经过思考后所能尽力表达出的那种严肃——再说一次,我永远都不会把你看作一个只会卖柯罗作品的艺术品商人?,对于我,在我很多作品的创作中,你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,没有你,这些画不可能在不幸和颠沛流离中仍保持一份平静。这就是我们的关系。
现在,画商们主要经营已去世艺术家的作品,所以他们和在世艺术家的关系变得很紧张。面对这样的关系危机,上面的话就是我一定要告诉你的事情。我为自己的事业付出了所有,还为此搭上了一半理智——搭上就搭上吧——但是据我所知,你并不在那些唯利是图的经销商之列,在我看来,你可以选择你的立场,并且你的行为都是出自纯真的人性,但是,你又能做些什么呢?
(1890年7月29日,梵高离开了我们,年仅37岁。)